超话黄v是什么颜色 ,[长篇](科幻悬疑系列) 今天你是什么颜色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个很滑稽的题目,人怎么可能变色呢?当然,人是不会变色的(科学上来讲),不过,我们常说,“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这也就不奇怪。要声明一点,这个故事与与这句话完全没有关系。我要说的这件事情,并不是某个人自身会变色与否,而是看待他的那个人是否正常。但我保证,这是事实,是我MISS JOY经历的所有不可思议的事情中,让人最容易接受的一件。
让我从头说起吧。
 今天你是什么颜色](https://www.6zmt.cn/zb_users/upload/catimg/d61b0ceb4e6625aa3df090545a849383.png)
( 1 )
YUKI马上可以卸下绷带,我们一群好姐妹全围在她病床前,没有她的家人,这个倔强的女孩子不顾家人的反对,三年前毅然报考了我们学校的油画系,这让她的医生父母留给了她一句话:“我们不会拿一分钱让你花在那些颜色上。”所以,她的这次车祸花光了我们几个的嫁妆和养老金。
最倒霉的是,那个车祸肇事者竟然不顾一切地跑了。有比这更损的吗!这样的男人(我想应该是男人),完全没有责任心,倒贴给我也决不考虑。应该说我旁边这位高医生相当绅士,对我们YUKI照顾得无微不至,还经常熬汤从家里带来,我们几个这几天都在寝室里偷笑,商量着还是不要来医院,免得我们的高医生没有机会表现优点。
YUKI不让通知她家人,因为这次车祸中,她受伤的地方是——眼睛。对一个画者来说,有什么比眼睛更重要,那该死的司机!高医生说,YUKI的眼睛并不是完全没有危险,因为她的视觉神经被一块很小的血块压着,那血块的确太小,当然也可以说没什么危险——是没有生命危险——医生总是把生命看得最重要,从垂死边缘回来的人,保住命就是最幸运的了。
我们几个屏住呼吸,看着高高(我们背地里这样叫他)轻轻地把绷带一点一点地裹在手上,一边说:“要是感觉眼睛疼,就说出来,不要勉强,知道吗?”
YUKI很听话地点着头。
上帝保佑,你可千万别说你看不见呀,要不我的嫁妆就打水飘啦。本小姐可是赌上了自己的终生幸福呀——当然,是夸张了一些。
“慢慢张开眼睛,慢慢地,对,有没有看见什么?”高高拿手在YUKI眼前晃着。
“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不是吧,YUKI不会是看不见吧。
“怎么啦,YUKI,看不见吗?”我们几个可是在你身上押了重注呀。
“怎么啦?有什么不妥吗,感觉得到光线吗?”高高的关怀充分显示他的职业道德。
“不,很好,只是有些模糊,我想才开始是这样吧,”YUKI笑着说,“我能看见你们,你们别这幅表情,JOY、SALLA、KETTY,我都能看见。你们放心吧。”
天,太好啦,刚才把我吓得。
“你是高医生?”YUKI果然看得见,她转头望向高高。
“是的,很高兴你的眼睛能康复。恭喜你。”
“太好了,那是不是说YUKI可以出院了?”KETTY说。
“出院是没有问题,但最好还要观察一段时间。”高高看着YUKI,似在征求她的意见。
“呃…我想是应该再观察一下吧,”YUKI说,“你们今天有课吗?我没事啦。你们回去吧。”
那怎么行!我这句话还没出口,SALLA就说:“那好,你好好休息,我们明天再来。”
说着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立刻明白过来。
( 2 )
我们猜想YUKI这几天在医院里肯定开心死了(白痴,谁住院会开心),凭我对YUKI的了解,让她三天不去画室,她就内分泌失调。这一次竟然主动留院观察,还说不是春心荡漾?
说来,他们也是两情相悦,YUKI眼睛康复后的住院费用都是高高垫着的。气死人,你们俩怎么不早点在一起,要不也不用我们垫嫁妆啦。开个玩笑,我们怎会是那样的人。再说,高高背地里告诉我,他会把我们三个垫付的费用还给我们。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所以说,祸兮福所倚,YUKI要不是被车那么一撞,也不会遇上高高这样的好男人。说来,真要感谢那司机。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一切很顺利。但是,YUKI不能一直不出院呀,还有一个月就期末考了,就算再如胶似漆,也不能不考试呀。
所以,我决定给YUKI做点思想工作。
我买了一束百合花,这是YUKI最喜欢的。我走到她病房门前,正准备敲门,忽然发现门是虚掩着的,我猜高高一定在里面。象我这么识趣的女孩子又怎么会这么唐突呢。我站在门边——偷听——等证据确凿,还怕你YUKI不承认?
“高医生,你实话告诉我,我的眼睛是不是一辈子只能这样了?”
“对不起,我想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我…那就是说…我永远不能画画了,是吗?”
什么和什么呀,YUKI的眼睛不是没事了吗,她不是能看见吗。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会为我做的一切负责任——我可以照顾你一辈子……”
越说越迷糊。
“负责任?怎么负责任?你如果真愿意负责任,我倒下的那一刻,你就该送我到医院,但你呢?”
那就是说,把YUKI撞倒的人是高高?
“那件事之后,我真的很懊悔。我不敢求你原谅我,但起码,可以让我照顾你……”
“我不需要你的施舍!我要出院!我要马上办出院手续。”
“YUKI,这不是施舍,我是真的…想照顾你…我……”
“够啦,对不起,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想这个时候我还是不要出现的好。
我想我明白了一些。是高高把YUKI撞倒的,然后他不顾YUKI,跑了。在YUKI被送到医院后,高高良心发现,要做YUKI的主治医生——或者说,是想让YUKI隐瞒真相。所以,他支付了YUKI的所有费用。那,YUKI的眼睛又是怎么回事,她说没事就是骗我们的,难怪她要求留院观察,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哪。她既然知道高高就是那个可恶的司机,她为什么不……,那她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真是越想越不明白。太复杂啦,告诉SALLA她们?人多好办事嘛。
但是YUKI不告诉我们就是不想我们担心,真是个倔强的丫头。
( 3 )
YUKI出院后还是在寝室里住,SALLA和KETTY两个人很高兴地给她大摆宴席,说是要到“米之味”去吃日本料理。
看着YUKI强颜欢笑的样子,我可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看来,YUKI不让我们知道是对的,她的眼睛到底怎么啦。
我们来到“米之味”要了一个单间,这里气氛很不错。她们要了几客不同口味的寿司,我自己要了一大碗“海味乌东”。
“YUKI,你不是从不吃芥末酱的吗,住了这么久的医院,转性啦?”KETTY笑着从YUKI手里抢过芥末酱。
“呃…芥末浆吗…我拿错了……”
“你要的是芝麻酱吧。”(YUKI的最爱)我顺手把瓶子递给YUKI时,我已经知道,她的眼睛真的有问题,这些调料都是用玻璃瓶装的,芝麻酱和芥末酱一看就知道,但到底是什么毛病呢。
晚上回到寝室后,KETTY要出去跳舞,问我们去不去,SALLA说要约会,我和YUKI都说不去了,KETTY这丫头真是活力宝贝,玩了一天还不累。
“YUKI,我的水粉橘红色没有了,把你的借我一下。”我想起来下周一要交设计作业手稿,我还没做哪。YUKI她们油画系的就好啦,不用象我们室内设计专业的,常常把作业拿到寝室里做。
“这个吗,是锡管装的,给你。”
“谢谢,”我接过一看,这根本不是橘红色,是橘黄色,不过标签上的“黄”字给摸掉了,就只有一个“橘”字,真是的,上面不是有颜色注明吗,没字也不看看颜色,“拿错啦。”
“是吗,那还是你自己找吧。”
我打开YUKI的画箱,发现橘红色颜料就在最上面,是用透明塑料罐装的,上面没有标签。真是的,颜色都分不清,还油画系的哪。等等,分不清颜色?今天YUKI还弄混了芥末和芝麻酱,那天她还说什么“永远不能画画”,难道,YUKI——色盲?
“YUKI,你看,这不是橘红色吗。”我拿着颜料在YUKI眼前晃了一下。
“哦,是呀,还是你自己找到了,真是的……”YUKI你又何必这样。
天,我的猜测没有错,YUKI真的色盲,我拿的根本不是橘红色——是翠绿色。
这一刻,我想应该是我欺骗她的时候了,“哦,我下去给家里打个电话。”(寝室是有电话的,但楼下的公话超市自然比较便宜,到楼下打长途,才是作为学生的我们省钱的正确选择。)
“喂,高医生吗,我是JOY,你现在有空吗?”
“现在吗,我在医院值班,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YUKI,是不是——色盲?”
“你不说我也知道,这样不行,她那么爱画画,你有办法的……”
“JOY,对不起,YUKI脑里的那个血块紧压着她的视觉神经,而且血块太小,唯一的办法只有等……”
“等?你是说等血块自己化掉?”荒谬!这一刹那,我真想马上说出他是凶手。
( 4 )
“JOY!”
我回头一看——YUKI——她怎么在我背后,她全听到了?
“对不起,高医生,谢谢你。打扰你了,再见。”我忽然之间有一种作贼被捉到的感觉。
“喂,刚才是不是……”
没等高高说完,我已经把电话挂掉。
“你都知道啦?这么巧,我下来买东西。”YUKI的确是一个很倔强的女孩子,此刻换成是我,一定无所适从。我明白她不把真相告诉我们原因,怕我们担心是真的,为了她的自尊,这更是真的。如此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又是如此的高傲,怎么可能在别人面前示弱——一个色盲的人居然想画画——这岂不是一个大笑话,你有听说过一个双腿残疾的人发誓说要成为刘翔第二吗?让人知道她眼睛的情况,她将失去一切的荣誉(包括她已经被内定为保送中央美术学院作研究生的资格),这件事被我知道,她就很难不去想是否还有其他人知道。但此刻,她如此镇定,为了那还残留着的一点自尊。
“我觉得你应该让我们知道。”我常常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可以解决很多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后来才知道,这只不过是我自己自信心爆满的缘故,当然,这是后话。
YUKI说,在她拆下纱布的那一刻,她就已经认出了高高,她在倒下的前一秒钟,记住了躲在车里的高高的样子;也是在那一刻,她发现她的世界没有颜色——只有黑、白、灰(从理论上讲,这都是复色),就象看黑白电视一样——除了,见到高高时,她看见的高高很奇怪,象是用单一的颜色画的素描,也就是说,她看见的高高全身只有一个颜色,只不过有明暗差别,其实也和看黑白电视差不多,只是有了一种颜色。更奇怪的是,她看到的高高有时候会变成另一种颜色。一般情况下,她看到的高高是黄色的,但是,慢慢地,会变成橘黄色,在她离开医院的那天,高高是橘红色。
这也够荒谬的,我问YUKI:“为什么不报警?”
我说完,马上笑了,我是明知故问。
我答应了YUKI不告诉任何人,但我想这一次期考,她一定过不了关。
我第二天一大清早就跑到图书馆。是的,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要不然,YUKI肯定要退学。说实话,我对YUKI的话不置可否,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现象如果是真的,那实在是太有趣了。
我抱了一大堆神经、眼科方面的书籍,在图书馆里“研究”了一天,根本没有任何一句话有写和YUKI的情况有关的。难道,YUKI说的一切都是假的——不,我从不怀疑她的真诚——难道是她的幻觉?
已经是晚上8点啦,我可真佩服自己,一天没吃东西,对科学的探知欲望竟然让我废寝忘食——倒,自恋狂。
我回到寝室的时候,KETTY告诉我一个让她兴奋不已的消息,下午6点多,高高打电话来把YUKI约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其实,他们俩真要是在一起,也未尝不是最好的结果。
到11点寝室统一关灯的时候,YUKI还没有回来,看着外面下这么大的雨,我笑着想,8成不回来了。
“JOY,你说,现在YUKI在干吗,哈哈。”关于KETTY的这个问题,我忽然间觉得很沉重,我当然很希望高高可以照顾YUKI,但是我总有种不祥的预感,因为我相信一切有因必有果,高高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当这样的想法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当然是和高高在一起嘛。”SALLA是一个爱情专家。
“具体一点,具体位置,哈哈。”KETTY还真是“俗”女。
“比如说……”我也知道这样的话根本不好笑,但为了让自己轻松点,也参与进来。
“你们俩好讨厌呀!”SALLA呀,何必虚伪。
“我们长着成年人的身体,当然要想成年人的问题。”我常说这样经典的话,以为自己很特别。(看来“古墓探密”那件事情后,并没有让我有多少启发。不好意思,有些偏题,关于那件事,有兴趣可以读一下拙作《汉墓漆画》。)
( 5 )
YUKI是早上10点过回来的,我们都还没有起床呢,我们三都不想起来,因为谁起得最早,就要负责买早点。我心里盘算着,要是YUKI回来的话,一定给我们带了早点,她是怕我们严刑逼供。
果然。
“三个懒鬼,起床!吃早饭。”
我看见YUKI脖子上的吻痕,我朝SALLA挤了一下眼睛。SALLA笑着说:“最近蚊子很猖狂。”
“夏天嘛,是比较活跃。”我说。
“没有啊,我昨晚睡得很好。”白痴KETTY。
“是吗?我还以为你被蚊子折腾了一晚上,眼睛都有血丝了。”我想我这句话好象不怎么含蓄。
“是吗,是吗。不会呀,我眼睛很红吗?”KETTY说着,马上照镜子。
“这都没关系,重要的是不要让蚊子叮的疙瘩太明显,要不然,一会出去怎么见人呀。”SALLA今天的比喻很大胆。
我和SALLA边吃边笑。YUKI很是稳重,不发一语,到阳台去洗衣服了。
吃完早饭,我和麦可去逛街。他是医科大的研究生,比我大6岁,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当然也是我的未来老公。
“JOY,最近YUKI怎么样,她的眼睛没什么吧。”
“哦,我正想问你,你要尽可能回答我。”
“好,你问,我有问必答。”麦可表现地很高兴,因为我从来都以为自己可以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这让身为男人的他很没自尊。
“你说有没有可能色盲的人能看见颜色,我是说,她看任何的一切都是黑白,但当她看见某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竟然是有颜色的——不是——那人是只有一种颜色的,哎呀,我都说糊涂啦。”
“你该不会是说的YUKI吧?”麦可好聪明。
我无奈地点着头,对不起,YUKI,我不是故意的。我只好把YUKI和高高的事情告诉麦可,当然我是有所保留的,我没有说出高高就是撞伤YUKI的那个人。
“这样的症状很奇特,你确定是真的吗?”麦可的眼神告诉我,他很有兴趣帮我查明原因。我想我跟他真是天生一对,对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有极大的兴趣,不过,他的兴趣仅仅限于与科学有关的事情,而我MISS JOY则不同,我认为现今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并不代表着不存在,古代人认为“天圆地方”,这在当时就是科学,所以我说,大部分人认可的就是科学,科学没有对错之分,只有被接受或被排斥。
我知道麦可是相信我的,在医学方面,他有无穷的探知欲,他说:“今天是星期天,我不想打扰罗教授,我们先去图书馆。明天我再去拜访他。”
图书馆?有用还问你?不过,我也不想扫他的兴。只好说:“好吧。”
我和麦可在他们医科大的图书馆坐了一下午,这两天坐图书馆坐到我屁股都变平了。
很无奈,一样没有结果。
麦可把我送回了学校。
我回到寝室,发现只有YUKI一个人在阳台洗衣服,老天。从早上到现在,她还在洗。哈,洗衣服也能洗得这么开心。一个人笑什么呢。
“YUKI!”不理我?
“YU——KI!”
“啊!你想吓死人呀!”哈,还恶人先告状。
“一个人傻笑什么呢!哦!你坏哟,想高高呀?”
( 6 )
“我哪有?我只是…JOY,你相信吗?但那是真的,你要相信我,它真的会变。”我看不出YUKI此时是兴奋还是恐慌,我只是觉得她是语无伦次,但我很有兴趣听下去,我相信她的话一定和她的眼睛有关,自从我知道她眼睛的情况——如果YUKI的话千真万确——那将是现今科学所无法解释的——这确实很让人兴奋。
“变啦?什么变啦?猴子都能变成人。你说清楚呀。”我之所以打这样的比喻,是因为我始终不相信“人的进化始于猿猴”这样的(荒谬)说法,在我看来,人就是人,猴子就是猴子,难道两个人长得相象,就一定有血缘关系?更何况是人和猴子。我这样说,只是要告诉YUKI,任何事情都会有人相信。
“我是说,”我看出YUKI害怕我不相信她,她能开口说出这件事情已经很让她为难,毕竟这件事情听起来确实有些荒谬,除了我,很少人会相信,“你记得我上次给你说的话吗。我说高高在我眼里的颜色是会变的。”
我立刻明白YUKI接下来要说什么,一个色盲患者可以看见某种颜色,而且还是对待某个特定的对象时发生的情况,这已经是很让人惊奇的科学现象(我之所以说这是科学现象,是因为当时我肯定这与我熟知的玄学无关),更让人奇怪的是,这还是一种会变的颜色,我不知道这次又变成了什么颜色。
“红色,火一样的红色,我看见的高高仿佛是从火中走来一样……”,我听着YUKI的话,忽然一震,她说的那种情景,让我昨晚那种恐惧的感觉越加强烈,但是,YUKI仿佛越来越兴奋:“那种红色,很漂亮,搀杂着飘动的橙色,仿佛是火焰的跳动……。”
我明白这个女孩子对于艺术的热爱是任何危险都阻挡不了的,她的那种形容真的很美,但是,那种莫名的恐惧比她的形容所给我的震撼要强烈得多。恐惧?我能断定那种感觉就是恐惧——莫名的恐惧。
幸好,YUKI接下来的故事,多少让我镇定了些,让我的思维又开始围绕着她的病情。
以下的叙述全部是YUKI的话,我相信那样的情景被我转述出来,一定会失掉它原有的韵味。
“你知道吗?他(高高)打电话给我,我,不想见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拒绝。他说他开车来接我,我想这样影响不太好,就约了在走马街的‘茉莉坊’见面。(这我是明白的,高高开车来接她,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YUKI爱慕虚荣。)
你一定不相信,我搭错了车,我一出校门,就看见1路车(她以为是1路车),我飞奔过去,那种急切的心情,仿佛我错过了这班车,就永远见不到他。(YUKI说这句话时,我感到一种她身上从未有过的坚定,我当然明白她搭错车的原因,恐怕是一时心急,看错了。)
我一路上不知所措,我一直在想我见到他时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不想看见他内疚的眼神,我要的是一种疼爱,不是怜惜,所以我每次看到他的眼神,我就无明火起,总要说一些话伤害他,好象他伤得越重,我就越开心。(人在年轻的时候总喜欢让心爱的人受伤,我那学考古学的姐姐,今年35岁的玛利亚常常这样说。)我没有意识到自己上错了车,自然也没有意识到车到了终点站。如果不是售票员提醒我,我可能还要一直坐下去。我下了车才发现,这是南门界(和走马街隔了两条街,看来YUKI是错搭了11路车),我本来打算叫辆的士,可能是虚荣心作祟吧,我准备走着去,反正也不远,就让他等等,反正也不会等太久的。
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我几乎还有十来步就可以走到走马街的时候,忽然风雨大作,天空一下子暗下来,我,我的世界仿佛也忽然间全没有了。(我这时候才知道色盲的人在晚上会变成‘瞎子’。)我想,即使我是色盲也好呀,最起码我看得见他,我突然好害怕自己有一天真的会瞎。我当时真的好无助,我不敢向前走,我只有站在原地,雨水的冲击让我一时间好后悔自己的决定,我不该去享受那种伤害他的快感。(此刻,我知道了YUKI有多爱高高,只有一种力量可以让一个如此骄傲的女孩子坦言她的懦弱。)
我一个人在原地傻傻地站着,我想起我包里的手机,当我摸索着拿出来的时候,居然没有了显示。(不知道是没电了,还是被雨水浸湿了。)那一刻,什么是绝望,我相信我已经完全体会到了。
就在我全身瘫软,想一下子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发现我眼前有一个小红点在一点点变大,我知道那是高高,但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做不了,我只有等。一点一点,我在等高高来到我面前,我知道他开车来接我了,他从车里向我奔过来,就像从火里跑出来一样。(我想,YUKI虽然看不见车子——应该是看不见一切,除了高高,但她却能断定高高是开车来的,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后来他们是开车离去的,二是因为高高开着车,YUKI只看到他的上半身,当他从车里出来时,身体会有一个伸展的过程,所以很容易知道原因。)
我站在那里等待着高高的拥抱,他跑过来紧紧地拥着我,我只想一辈子就这样。(YUKI的这句话,听起来确实有些肉麻,不过在她自己看来,只是把她的感受说出来罢了。她自己也洋溢在那一刻的永恒幸福里。)
后来,天太晚了,就……”
“行啦,行啦,明白,不用说得那么详细。”接下来的事情我可没什么兴趣。
“我刚才是不是……”YUKI此时此刻才意识到她刚才的失态,她的每一个字都在告诉我她有多幸福,我想她也只能告诉我了。我成了唯一知情人。
( 7 )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麦可的电话。他说他把事情告诉了罗教授,但是因为他也不是知情人,也说不清楚,所以,罗教授想见我。
我和罗教授自然是很熟悉了。大概是他对我的脑部结构很感兴趣,总说我的想法奇特,但很让我欢喜的是,他从不否定我的想法。
我们来到罗教授的家里,这个地方我并不陌生,特别是他放在书桌上的那个烂陶片,我就更熟悉啦。(缘由请见拙作《汉墓漆画》)我把YUKI的情况给罗教授作了详细的汇报——除了高高是撞伤YUKI的那个人。
“理论上,这很难解释,”罗教授点了一支烟,当他很认真地思考一件事的时候,这是一个明显的示意,“人的大脑很复杂,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块小血块,这未免太牵强。这个小血块应该是导致YUKI色盲的直接原因,但为什么她可以面对高高时,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就太不可思议了……居然还会变色……你们想,这有没有可能是YUKI一相情愿的想法,我们不能完全肯定车祸没有给她留下其他的后遗症。”
“您的意思是,妄想症?这是YUKI的幻觉,”我也曾经有这样的想法,但自从昨晚以后,我完全相信YUKI的话,“罗教授,我曾经和您的想法一样,但是,如果一切都是幻觉的话,前晚的事情又怎么解释?您想,照刚才的假设,YUKI要看见有颜色的高高,前提条件是,她必须要能看见高高,但是,那晚下大雨,YUKI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自然也看不见高高,但她为什么又只能看见高高,还是红色的高高?”
罗教授一边掸着烟灰,一边轻轻点头:“有道理。这种情况只在他们两人之间出现,这就证明,高高对YUKI而言很特别。”
“他们两人在谈恋爱,你爱的那个人对你来说,自然是最特别的。恋爱中的两个人就象两块磁石,互相吸引。”麦可深情地望着我,我噗嗤一笑,很是不习惯他的这种突如其来的表白。
等等,磁石?磁场?对啦,就是磁场,人体的磁场。我兴奋地说:“罗教授,会不会是人体的磁场?”
我很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罗教授也熄灭了手中的香烟。
“我是说,我们常说,谁和谁有缘分,相隔千里,也能相遇,这会不会就是因为他们的磁场互相吸引的缘故,就象相爱的两个人,他们凭什么互相吸引?我们所说的那种感觉,会不会就是对方磁场所发射的磁电波,扰乱了我们正常的磁场,使我们的磁场发生波动,从而,我们会有心跳加速、心疼的感觉。”
“这样的话,那YUKI只和高高相吸引,是高高的磁电波扰乱了YUKI的磁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YUKI只有看见高高时,会有颜色。因为,只有高高的磁场才能吸引YUKI——YUKI真的爱上了高高,她的磁场愿意接受高高的磁电波——如此的深爱,看来,YUKI很难爱上其他人。所以,只有高高,才是有颜色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天大雨的夜里,YUKI在看不见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却能看见高高,确切地说,不是看见,应该是人体磁场的吸引。”麦可不愧是医科大的博士研究生,一点就明。
“不错,那天夜里,YUKI看不见任何东西,是高高的磁电波影响了YUKI的大脑,然后,YUKI的大脑给她的视觉神经发出命令,也就是说,高高的形象通过他的磁电波传达到了YUKI的视网膜上,但由于YUKI本身是看不见任何东西的,那是因为她的磁场不接受除高高以外的任何磁电波,她看得见高高,不能说是看见,那是一种反映,象镜子的反射,那只是一种映像,但并不能说不是真实存在。”我相信我的观点可以解释这些原因。
“那为什么YUKI眼里的高高会变颜色呢?”我知道罗教授心里已经默许了我的论证,但因为这是“超科学”的,他作为一名脑科权威,决不能亲口承认这些。
“很简单,同样是磁场,因为从开始到现在,高高给YUKI的感觉是一步步加深的,或者说,YUKI的磁场越来越愿意受到高高的磁电波的干扰。从颜色学的角度上讲,这是可以解释的。最开始,高高在YUKI眼里是黄色,黄色,是背弃的颜色,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里,叛徒犹大就是身穿黄色的衣袍,这表明最开始,YUKI认为高高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是背弃了她的人,也是背弃了他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道德的人。”我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把真相全抖出来,我看见他们两知道YUKI是被高高撞伤的以后,都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
他们俩的沉默,暗示了我继续说下去。我接着说:“要知道,橘黄和橘红都是富有生命力的颜色,是让人感觉强烈的颜色,是属于恋爱中人的颜色,它们是属于绝对的暖色系。从黄色到橘黄、橘红,正说明了YUKI在慢慢爱上高高,这种感觉随时间的推移而越加强烈。到那天晚上,YUKI说,高高仿佛是火一样的红色(我说到这里,又是一震,那种莫名的恐惧又上心头),这也就表明,在那一刻,YUKI完全爱上了高高。红色是最强烈的颜色,更何况它还象火一样(我觉得说高高从火中跑出来,这样的比喻很让人恶心)。”
“也就是说,高高的磁电波扰乱YUKI磁场的能力越来越强?”麦可和我之间的默契,总是可以不时地表现出来。
我赞许地点着头,又说:“应该说是YUKI的磁场越来越愿意接收高高的磁电波。高高给YUKI的感觉越强烈,YUKI的大脑给她的视觉神经所传达的命令也就越强烈,也就是说,反映在YUKI视网膜上的映象也就越强烈。”
“磁场?这个说法很有意思。”罗教授的这句话分明就表示了他的赞同。我心里暗笑这些“权威”的虚伪。
我接着又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有时候在接电话之前,就能预感是谁打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就和人体的磁场有关系。是对方的磁电波通过电话线传达到我们的大脑里。”
“照这样说,我们如果无法预感到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就说明我们本身不接受那个人的磁电波?”罗教授又点上了一支烟,这表明我的话值得他考虑。
我很高兴看到罗教授这样的反应,就又说:“原则上,的确是要我们的磁场愿意接受某个人的磁电波才行。”
一下午的讨论很让人顺心,到我们都觉得饿的时候,已经快8点了。罗教授留我们下来吃晚饭。
晚饭后,他说:“我有个朋友是眼科界的权威,你们可能听说过——杨成林教授。过几天,他要到我市参加一个研讨会,到时候,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罗教授口中的这个杨成林,说来其实罗教授也不太熟悉,只是有过几面之缘。但我听说过他的确是一个大人物,他的好多篇医学论文都在国际上获过奖。我也很想见见,我一向很喜欢和这种“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的。
( 8 )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表现出对YUKI眼睛的浓厚兴趣,如果你揭开了这么多人无法解释的奥秘(虽然,这可能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那你一定会把象YUKI这样的人看成是你的战利品。(我虽然觉得这样的想法有些心理变态,但是过高的自我评价的确可以掩埋一切。)
我很在意高高在YUKI的眼里是不是又变了颜色,因为这对我的理论是否正确,是很重要的凭证。不过,YUKI说,一直是那样的红色。(其实YUKI的原话是“一直是像火一样的红”,但因为我挺讨厌这样的比喻,所以更改了一下。)
这几天里,我很盼望那位杨教授的来临,如果他也承认我的推断,那对我这个爱慕虚荣的小女生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但是,我完全想错了,并不是每一个“权威”都像罗丙坤教授一样。我们的会面是在上一次和罗教授交谈后的第5天,地点还是罗教授家里。我把YUKI的情况完整地告诉了杨成林教授。(包括高高是肇事者。因为我觉得实在没有隐瞒的必要,他们可没有我们这些小女生这么小心眼。)当然,我的理论也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这些理论已经在前面讲得很详细,这里也就不浪费时间了。)
“哈哈,小姑娘,你的想象力很丰富。不过,科学要讲究证据,不是妄加揣测就行了。”这位杨成林教授似乎把我的推论看成了一个大笑话,真是让人恼火。
我 自然是不会放过要教育一下这位“权威”的机会——教会他学习尊重别人的意见,即使不赞同,也不可取笑于人:“那杨教授的意思是……”
“这不仅仅是眼科上的案例,在心理学上它也可以成为典型的案例。完全色盲的病患决不可能看见颜色,更不用说是会变的颜色,”对于这位的权威的坚决,我不知道说他是自信还是狭隘,扬帆航行在自己眼前的这片湖泊里,他还以为这就是全世界,这样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在真正的海洋里驰骋的魅力。
杨成林继续说:“这个个案有两个关键,一个是那个小血块,是导致色盲的直接原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小姑娘,这没意见吧。”
他转头向我,对于这一点,我自然不会有任何怀疑:“当然。”
“很好。另一个关键——颜色。你也说你那位朋友爱上了那位医生(这位‘权威’好象从来不习惯记住别人的名字),是不是。那就是说那医生在她心里很特别,所以,她下意识地把那位医生看成是有颜色的……”
“杨教授,照你这么说,你认为我朋友精神有问题,”我真有些气急败坏,虽然我曾经也以为是YUKI有妄想症,但那天已经证明不是YUKI的一相情愿,于是我问,“那,杨教授,我朋友那天夜里,在完全看不见任何东西的情况下,为什么能看高高?”
“你是说那个医生?我说过,小姑娘,这都是你那位朋友的幻觉。你敢保证她说的话都是真实的?我们无法肯定一个正常人说话的真假,更何况她不是一个正常人,她出了车祸后变成色盲,很难说她的精神上是正常的。再说,她是一个学画画的,喜欢那些无用的颜色,成为色盲后,心理压抑,所以只有凭记忆想象那些颜色,为了使她自己相信她可以看见颜色,她把对象安排为一个她深爱的人……”
对于这位“权威”对我朋友的侮辱,我终于忍无可忍:“杨教授,请你尊重我的朋友。你说她精神有问题?看来,医院的检查也比不上你的几句话。(本来我这话也没有错,作为一名‘权威’,没有实际地检查病人,就做出这样的结论,根本就是违背了‘以实验论证结果’的医学原则。)”
我的这些话显然使得气氛一下子僵硬起来,不过我不在乎,这样的“权威”,得罪了也罢。再说,他的言谈中蔓延着对艺术的不屑,这就更让人不可理喻。
“JOY,你让杨教授把话说完嘛。这也是就事论事,我们不都是在想办法帮YUKI吗,”麦可这时候跑出来打圆场(罗教授就一直没说话),“杨教授,对不起,请继续。”
“好,不过,我希望我接下来的话,不要有人打断我。”
什么态度?我郁闷地吐了口气,麦可皱了一下眉头,示意我不要冲动。
“我可以接着解释刚才的问题。我依然坚持那一切是不可能的。你朋友那天晚上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包括那个医生。她认为她看见那个医生的情景,是她事后的想象,因为那一刻的拥抱深深触动了她,她就在深层次里下意识地虚拟当时的情景——小姑娘,你的这位朋友病得不轻呀!”
我不敢相信地摇着头,这表明我也同意了杨成林的意见。一切都是 YUKI的幻觉,是YUKI车祸后的后遗症——妄想症。这也解释了YUKI眼中的高高会变色的原因——全是幻觉。
这一次的会面很不愉快,让我恼火的不是杨成林的自大,而是我对于自己需要重新估量。
( 9 )
自此后,我完全没有办法正常地看待YUKI,她的快乐、忧伤,在我看来,都显得不正常。我很懊恼自己这样的想法,它让我觉得自己很卑劣,原来,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个自大又无知的白痴。
我很希望我可以帮到我的朋友,或许,这也可以满足我那自以为是的自尊心。于是,我拨通了杨成林的电话,请求他见见我这位可怜的朋友,虽然在他眼里,YUKI可能已经不是一名眼睛有疾患的病人,而是一名精神病患者。杨成林说,心病还需心药医,他只能做一个初步的检查。我们约在第二天早上10点,医科大罗教授的个人实验室里。
我说服了YUKI。我告诉YUKI,说罗教授想见一下她,我不敢实说见她的其实是杨成林,因为,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麦可和罗教授,已经是让我觉得很内疚的,更何况还有个根本不认识的杨成林,这也就让YUKI很难不去猜测我是不是还告诉了其他人,再则,YUKI要是知道她见的是眼科界的“权威”,她一定会有种被当成白老鼠让人研究的感觉。所以我只是说,是罗教授听说她最近不太顺意,想见她,但又不方便到我们宿舍,所以就约在他的实验室。我估摸着平时YUKI对罗教授很是敬重,她应该不会拒绝。
什么叫做“好心办坏事”,在我身上充分地体现出来,后来,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后,我才后悔不已,如果我没有让YUKI和杨成林见面,之后的一切说不定都是风平浪静的。
但世事总是难料,世上一切都有因果,而我仿佛就是那根线。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位杨成林教授竟然就是YUKI从不愿提起的她的医生父亲。当我打开门,空气仿佛在那一刻瞬间凝结了,我不懂杨成林看见YUKI的表情,我只觉得很不礼貌,我自然不会知道站在我身后的YUKI的表情,只听YUKI忽然道:“对不起,JOY,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我以为是我的胡乱安排气坏了YUKI,忙转过身,想拉住她,这时我身后又传来杨成林的冷笑声:“走啊!走啊!象三年前一样,你妈被你气得现在还躺在床上。哼,你这个不孝女,要走是吧?那就走呀!”
YUKI被震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想我此时的震撼超过他们任何人,凑巧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只是今天特别巧。我偷偷望了望杨成林,他现在的样子也许是他从没有过的,仿佛有这样一个女儿是他人生最大的挫败。
我退出了房间,把这两间房子留给他们父女俩吧。难怪杨成林言谈中充斥着对艺术的无知与不屑,原因都是因为YUKI不肯报考医科大。他说我这个朋友病得不轻,看来他在医好YUKI之前,是应该考虑一下他自己是不是心理健康——有偏执症的人作医生可是很危险的。
我打电话把麦可约出来。我们在麦当劳选了两个靠窗的位置,我什么也不说,麦可什么也没问。我们买了一大堆汉堡包、薯条放在桌上,一直坐到晚上了9点。我真不知道怎么面对YUKI,她在她父母眼里是如此的骄傲,而我今天却葬送了她全部的自尊。我想他父亲杨成林教授会想方设法医好她的,但她会接受吗?她会不会认为这是她父亲的示威或是施舍?
这些疑问憋在心里让我有想吐的感觉,终于在回学校的路上,我给麦可坦言了一切。麦可的震惊没有我想象的强烈,他愣了一会,马上就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人在生病时总是很脆弱的,谁不希望这时候有家人在身边,他们毕竟是父女俩,嘴上闹得厉害,但哪有隔夜仇。我们这些天不都是为了帮YUKI吗。现在知道杨成林教授就是YUKI的父亲,他一定会想办法治好YUKI,这不比我们瞎忙活好吗?”
麦可的话很是让人宽慰,正是事无绝对,再倒霉的事情说不定也暗藏幸运,就像YUKI和高高。
( 10 )
事情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尴尬,也许是我一直太无视别人的宽大,任何人在我眼中,都会有人“应有”的缺点。就象我以为YUKI会怨恨我——其实不然,她告诉我今天她和她父亲整整沉默了两个小时,终于她说出了第一句话:“对不起,爸爸。”
YUKI高兴地说,她答应她父亲考试完毕马上回家——她三年来第一次回家。
就这样,我们怀揣着好心情睡到了第二天。
一觉醒来已经10点,YUKI说要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高高,可高高的电话总是处于关机状态,打家里电话又没人听,这使YUKI很是心神不宁。
我劝慰YUKI说,高高一定是在手术室作手术。(我不知道几个小时后,这句随意的话竟然变成了一个让人晕眩的现实。)
吃过午饭,我和KETTY准备出去逛街,SALLA也准备出去约会,本以为寝室里就只会剩下YUKI在那里等高高的电话。
正准备出门,忽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那种莫名的恐惧一时间如洪水宣泄般从心中轰然涌出,这种熟悉的感觉,让我想吐。
YUKI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但紧接着她的动作使我们所有人都愣住了,应该说,她没有任何的动作,只有电话从她手里滑落。
我,恐惧感越盛。
从电话滑落到她飞奔出门,不会超过3秒钟,而我们3个从她离开到自己有所反应,超过了5秒钟。
等我们回过神来,YUKI应该已经跑到楼下了。
我们一路追赶YUKI,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这也就是我们追出来的原因。
一路狂奔,居然来到的是医院。不知道是高高有事还是杨成林教授有事。我还在犹豫着,KETTY一把拉着我就往里面拖。
我们跑到询问台,值班护士告诉我们YUKI往3号手术室去了。(因为YUKI在医院呆了很长时间,所以医院的护士大部分都认识。)SALLA和KETTY问明3号手术室的位置,就急忙跑去了。我刚一转身,又急忙停住,我问护士:“3号手术室里的是不是…高佐治医生?”
我不希望我的猜测是正确的,但护士的沉默告诉我,我猜对了。
“什么时候送来的,到底是什么意外?”我所问的问题仿佛早已在我心里存在,只是在等一个适当的时机罢了。
“车祸…我听说是车祸……”护士的回答支支吾吾,好象有很多要说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又是车祸?
我一把捉住护士颤抖的右手(我知道她下意识地整理档案,是想逃避我的问题):“我是高医生的朋友,请你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一切。求你了。”
护士拗不过我,只好说:“你先放开我呀!”
“哦!”我忘了我自己是空手道黑带。
“其实,我也是听说的。送高医生来的陈救护员说,在高医生车子里有两个酒瓶子,说高医生可能是酒后驾车……”
高高不会是这么不稳重的人呀,喝酒驾车,不是他的风格。这里面一定另有隐情:“还有呢?”
“我确实只知道这些,那边有警察在做笔录…你过去看看吧……”我敢断定这个护士还知道些什么,但她为什么害怕呢,有什么不能说呢。
我想如果要尽快知道什么,还是问警察来的好。
而这个警察给我的回答,仿佛是把我忽地扔进了冰窖里,我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车子爆炸…全身着火……”这和YUKI的话不谋而合——就像从火里跑出来一样——这是早已安排好的预示吗?
我没有办法把自己从恍惚中拖回来,我的眼睛没有目的地扫射,我不相信这是YUKI早已预料到的。我不住地摇头,却让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丘德麻葛(祭司)。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件事莫非与“马兹达新生教”有关?
我急忙追了出去。在医院后门的小巷里,我见到了丘德麻葛——果然是他。他背对着我,好象就等我来找他。
“尊敬的麻葛,好久不见。不过,好象只要你一出现,就准没好事儿。”我冷笑着说。
“这是火神阿胡拉·马兹达的旨意。你是受阿胡拉·马兹达祝福的人,你应该相信。”
哼!这群利用“祆教”(祆教徒自称“马兹达教”)教义牟利害人的邪教徒,自称什么“马兹达新生教”,把光明的祆教涂染得如此血腥。
“火神阿胡拉·马兹达选中了你朋友的灵魂作为火种,同时选中了高佐治医生作为此次祭祀的执行者,但是,高佐治医生背弃了对阿胡拉·马兹达承诺,他只是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丘德说得慢条斯理,好象他一伸手,就可以毁灭一座城市。
“少胡言乱语!你们这群侮辱了祆教光明教义的魔鬼,根本没有资格侍奉火神阿胡拉·马兹达,难道《阿维斯陀经》(我国称《波斯古经》)中的《耶斯那》(祭祀书)中有说,用鲜血献祭阿胡拉·马兹达吗?是你在车上作了手脚,还是你在酒里下了药?是你害了他们俩!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复兴祆教,其实这全是幌子,一群杀人凶手,骗子!”我对于这种邪教,一向是非常反感。他们侮辱了祆教的教义,我说得如此的铿锵有力,仿佛我真是一名虔诚的祆教徒。
“注意你的措辞。你早晚会相信这是火神阿胡拉·马兹达的旨意。要不是你身上的护身符,你刚才的言语足以让你致命——好好留着它。你记住,阿胡拉·马兹达要的东西,没人可以阻拦。你朋友的灵魂,阿胡拉·马兹达一定会得到。”说完,丘德就要离去。
我追着他出了后巷,却见不到他的人影——该死,溜得真快!(关于我和“马兹达新生教”的渊源,详情请见拙作《汉墓漆画》。)
我摸着胸前的护身符,不由得想,YUKI是被选中的祭祀品,高高是献祭人,他们俩从一开始就有关系。YUKI色盲,说不定使她的另一种能力增强——某一方面残缺的人在另一方面的能力较正常人突出,就好象失明的人听力特别强——她有了预知的能力,预知高高“从火中跑出来”——只是她自己不知道。那黄色代表的是背弃,高高背弃了他的誓言,红色代表的是火——也就是说,YUKI看见的从黄色到红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高高从背弃到死亡的过程。
我马上打了一个寒战,但我始终不相信那些神棍有这样的能力。我想我应该马上回医院。
( 11 )
我回到医院,直奔3号手术室。
手术室门上的灯还亮着,YUKI她们都坐在一边。我们一直等,期间主治医生出来了两次,但都没有回答我们任何问题。所以,我们还是一直等……
我看了看表,已经是晚上10点,高高在里面恐怕已经抢救了整整10个小时了。我又想起了丘德的话——在我的心里,已经做好了让高高死去的准备,但我很希望,他可以坚强地活着,YUKI不就是一个例外吗?并不是那群神棍想让谁死,谁就不能活。
但世事总不遂人愿。车子推出来的时候,高高被掩在白色被单下。我不忍看见高高留在这世上最后的样子竟然如受炮烙一般,我自然不会让YUKI看见他的样子。高高就像YUKI的太阳,是她生命的全部颜色,应该让高高最好的一面永远留在YUKI心中。我准备拖住YUKI的身子,但,已经晚了,被单顺势滑下,我还没来得及反应,YUKI已经晕到在地——她不敢相信,那是曾经和她缠绵的身体。
杨成林这时候跑来抱起YUKI。其实,我早就发现了他,他一直躲在拐角处,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和他有关。既然他和YUKI已经和好,这时候,他更应该担起做父亲的责任,他躲——只证明他心虚。我不会去相信丘德的话,虽然我无法证实那是捏造,但他也没有让我完全信服的理由。我只相信事实。现在的事实就是,杨成林与这件事情有关。而知道这件事情的,就是那个值班护士。
我去找她的时候,她们已经换班了。所以我决定明天一早就来问个明白。
我在床上想了一晚上,摸着胸前的护身符,它让我动摇了科学地分析YUKI病情的决心。直到凌晨3点,我才睡去。
一醒来,我就直奔医院(翘了4节室内材质课)。
昨天那位护士果然还在询问台。
“你信不信这世界上真的有鬼?”我已经盘查了她20分钟,虽然我断定她知道什么,但她就是不说,所以,我只好利用这个所有女人都害怕的话题。
“你和高医生也算同事一场,太绝情的话,鬼都讨厌……”我说完,马上作了个鬼脸,她还真被吓到。
后来,这位护士说,她昨天一早经过院长办公室门口,听见里面有个人叫院长马上辞掉高高,院长口口声声尊称那人“杨教授”。不是杨成林是谁。
我来到YUKI的病房,看见杨成林很憔悴,我本不忍心在这时候质问他,但是,此刻也许是他最脆弱的时候。
“杨教授,守了一夜?这么爱你女儿,又为什么要让她和心爱的人阴阳相隔?”
杨成林的脑袋耷拉着一动不动:“都知道啦?”
杨成林说,那晚他与YUKI和好后,他帮YUKI检查了眼睛,他发现自己医好YUKI的把握只有一成(也就是说,没有可能),刹那间挫败感涌上心头。他没有在YUKI面前表现出他的无能为力(他们父女俩同样那么骄傲),送YUKI回学校后,他只身回到“香格里拉”大酒店的他的房间。他完全瘫软在那张大沙发里,回想起显微(YUKI的中文名字——杨显微,作父母的自然不会知道我们的英文名,这都是我们自己取的)那么可爱的样子,他一直钟爱这个女儿。即使是三年前,她不顾一切报考油画系,作为父亲的他也决没有怀疑过他女儿的坚强和优秀。当时,他的记忆随着脸上泪痕的延伸而不断向前延续,回想起第一次见到这个可爱的、浑身赤裸裸的小宝贝时的情景,慢慢地,他觉得很累。他闭上了眼睛,在梦里和显微一起放风筝。忽然,风筝断线了。他急忙随着风筝飘落的方向追去——却看见一个干瘦的小老头拿着风筝向他走来,他的衣服很奇特,好象几千年前中亚人穿的衣服,他的头很小,脸很皱,皱到你要是放一支铅笔在他的额头上,那笔也决不会掉下来,他不象是汉人,倒象是新疆人(杨成林的意思是像外国人),那老头对他说,是高佐治扯掉了显微的风筝线,是他让她再也快乐不起来。说完,老头就消失了。杨成林回头找显微,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在慌乱中醒来,发现自己一身冷汗。回想刚才梦中的情景,老人说,是高佐治扯掉了显微的风筝线,而事实上,是高佐治害得显微色盲。刹那间,他把所有的一切都推在高佐治身上,他觉得这样的人没资格作医生。(后来的事情,自然就如那值班护士所说,这里也没必要多写。)但万没有想到,高佐治一时想不开,醉酒驾车,竟然……
听完杨成林的叙述,他所说的那个老人,很象是丘德。杨成林肯定地说,他决不认识那人。那为什么丘德会在他梦里出现呢?只有一种可能——催眠。而且,杨成林的做法很明显是他受到了“暗示”。
丘德应该是在杨成林半睡半醒时对他进行的催眠(至于他是怎样溜进杨成林房间的,我想这种人自然有他的办法),毕竟,在一个人意志最薄弱的时候,进行催眠是最有效的。每一个人在完全进入睡眠状态之前,都有一段意识很模糊的时间,眼睛没有合上,但神智已经不清醒了。丘德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对杨成林进行催眠的。因为,杨成林的眼睛并没有完全合上,所以,丘德的样子通过视网膜反映到他的大脑里,再结合丘德在杨成林面前说的那句话,所有的一切都影响了杨成林的梦境。丘德通过梦境控制了杨成林。这句话听起来很是玄妙,其实道理很简单。人,总是以为梦境中的东西很不可思议,对于我们无法解释的东西,我们总是喜欢加以猜测,越想就越觉奇妙,最后就下意识地相信梦境预示着什么——包括这位眼科权威,杨成林教授。
这一次,我答应了杨成林不告诉YUKI,这次我是完全的无可奈何,我自然是不希望YUKI知道杀死高高的人会是她老爸。
过了一天,杨成林打电话来说YUKI醒了。
我买了一束百合插在她床头的花瓶里。YUKI两眼无神——因为她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杨成林说,YUKI倒下时,头部受到撞击,血块移位,压制了视觉神经,这一次,是真的没有了任何颜色。
没有了高高,YUKI就等于没有了整个世界,能否看见,可能真的无所谓了。只有她的嘴不停地张合,反复说着一句话:“今天,你是什么颜色?”象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拿着一个永远不停的留声机。
尾 声
一个月后,我接到杨成林的电话,他说已经联系了美国曼哈顿第2联合医院,他决定把YUKI送到那里医治,希望我过两天可以到高高的墓上帮YUKI献上一束百合,就当是最后的道别。
我问到YUKI的病情,杨成林说,还是那样,像丢了魂儿一样。
我叹了口气,想起了丘德的话——你朋友的灵魂,阿胡拉·马兹达一定会得到——宗教的力量在于坚定人的意志,决不是对人性的毁灭。
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龙居山陵园。我怕我要是来晚了,说不定YUKI就飞走了,我也就失信于人,高高说不定也会怪我。
高高的墓碑与众不同,在他下葬那天,我就注意到,他的墓碑正面靠左的地方,有一串奇怪的文字——决不是花纹,虽然弯弯曲曲,我一个不认识,但我可以肯定,是古波斯文字,和我上次在汉墓里见到的古波斯文很相似。所以,我早就拓了下来,带给玛利亚。玛利亚姐姐翻译了差不多两周,才告诉我说,她只能确定几个字——火、罪孽、阿胡拉·马兹达、遗弃、孩子。
这已经足够了。昨天杨成林给我电话后,玛利亚姐姐就来了电话,告诉我她的劳动成果。所以,今天我来这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解开我心中最后的疑惑。
墓碑是高高父母所立,他们允许自己儿子的墓碑上刻着古波斯文,这决不是为了装饰吧,也就是说,高高和墓碑上的文字肯定有关系,进一步说,是他家人都和这文字有关系。如果我猜得没错,这段古波斯文应该是:“愿圣洁的火洗刷他的罪孽,愿阿胡拉·马兹达不要遗弃这孩子”。
可见,高高的家人都是祆教徒——应该说是“马兹达新生教徒”。丘德说过,高高是被选中作为那次祭祀的人。在祆教教义中,负责祭祀的只能是祭司,祭司一般出自圣职家庭,父子世代相传,并且只能和圣职家庭内部通婚。(虽然“马兹达新生教”并不是纯粹的祆教,但为了名正言顺,就必须遵照祆教教义。)
难怪高高的样子并不像汉人,他的名字也不象汉人名。如此说来,高高连续违背了两次命令。第一次,杀掉YUKI,他没有办到。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不顾医生的道德舍YUKI而去——他是蓄意谋杀;第二次,他还爱上了YUKI,和她发生了关系,违背他们的通婚法则。所以,教中派出了丘德执行惩罚。按惯例,执法者必须与被执行者同辈或是更高级,那高高应该是教中的“麻葛”(祭司)或是“麻培特”(教士),这两者是同级,再低一级就是“埃尔伐特”(事火祭司)。
看来,高高并不是纯粹的“马兹达新生教”教徒。新时代的年轻人,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又怎么会相信这些呢?只怪他身上流着祭司的血。难道教徒的孩子就一定要信教?他们无法选择他们的出身,难道就无法选择他们的信仰?居然连选择爱一个人的权利都没有。身为真正祆教徒的人们,一定不会希望自己的坚贞信仰变得如此血腥。
我一直不相信,高高是因为当不了医生,一时气急,醉酒驾车。应该说,高高知道他的“背叛”会招来惩罚,而他一定见过了丘德,他知道他的下场一定很难看。因为无法消除这种可怕的阴影,他选择了逃避——不停地喝酒,最后导致车祸。
我忽然间大笑起来,我嘲笑“马兹达新生教”搞出那么多事,根本是多此一举。高高他们对这些教义一定是又恨又怕,早晚是会被吓死的,就象高高的死,丘德何必还要利用杨成林,让一个可怜的父亲内疚一辈子。
我的推断到现在并不是完全合理,但我面前还有一条线索,如果我的推断合理,高高的墓碑前的石盒里应该没有安放他的骨灰。(出殡那天,高高父亲说会火葬。)
在祆教教义中,水、火、土被视为神圣,土葬、火葬和水葬自然是在禁止之列。祆教实行的是“天葬”。(“天葬”的详细情况,请见拙作《汉墓漆画》)
所以,对不起,高高,我要看看你到底在不在里面。
我用力推开石盒子上的顶盖,里面居然安放一个骨灰盒,我扯下盒子上的封条,发现里面居然有“骨灰”。
不可能,高高的父母能够在墓碑上刻下那样的字,就可以看出他们有多虔诚,他们决不会违反教义。如果这墓是真的,那么高高和他的家人就不会是“马兹达新生教”的教徒,墓碑上就不应该有那些字。如果这墓是假的,那高高的尸体一定被运往某个山丘上进行“天葬”,那这些灰一定不是他的骨灰。我决定拿一些“骨灰”回去找麦可化验,我用面纸包着揣在背包里。然后把骨灰盒放回原位,我用力把石盖移会了原位,我正准备起身,忽然后脑一震,眼前一黑(自然是被人打了)……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麦可在我旁边睡着了。
后来听护士说,是有人送我来的。我问,那人呢。她说,把我送来就走了。
我想起了包里的“骨灰”,可怎么也找不到。麦可问我找什么。我犹豫了一下,说,没什么。
他们不让我找到最后的证据,就是让我不要再管这件事。也许,若不是我身上的护身符,我可能已经被杀了。
哈,我叹了口气,感谢阿胡拉·马兹达,愿你同你真正的信徒们同在。
相关文章
- 详细阅读
-
电脑怎么弄视频壁纸(电脑怎么弄视频壁纸win10)详细阅读

去各大软件工具平台或者百度搜索“视频壁纸软件”,下载视频壁纸工具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2 下载完成后进行安装,建议安装在非系统盘非C...
2022-09-12 77928
-
酷酷的滕那种文字视频怎么制作的(类似于酷酷的滕那种视频是怎么做的)详细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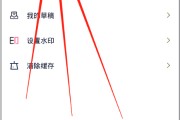
酷酷的滕的视频怎么加的字幕? 展开 #xE768 我来答 分享 微信扫一扫 新浪微博 空间 举报 浏览30 次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
2022-09-12 74842
-
cj视频制作(cj视频是什么意思)详细阅读

1、把照片做成视频,推荐用 数码大 师 简单易上手 人人都会用的精美相册制作软件 点击 添加相片 按钮,悉数导入相片,加上旁白注释文字特效音乐视频 点...
2022-09-12 66695
-
异地恋怎么视频做吗(异地恋开视频怎么做那个)详细阅读

总而言之,我认为异地恋是没有必要每天视频通话的,因为我和我的女朋友只是经常聊天,但并不会视频通话,而且如果我们相互思念对方的话,会在放假的时候一起出去...
2022-09-12 1388
-
彩视视频制作(彩视视频制作收费吗?)详细阅读

1打开彩视APP主页后,点击右下角的个人信息头像2进入到个人主页,点击彩视我的作品一项,选择一个视频,点击进去3接着点击播放窗口右下角的更多菜单,弹出...
2022-09-12 1601
-
小视频宣传片怎么制作(小视频宣传片怎么制作的)详细阅读

导读信息爆炸时代,我们每天接收成千上万条信息信息的几何式增长使企业在进行宣传推广时不得不绞尽脑汁推陈出新,吸引消费者的眼球短视频的兴起,为企业宣传推广...
2022-09-12 1414
- 详细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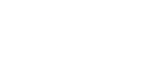


发表评论